商業(yè)航母:無形之手順勢而為
回顧即將過去的2007年,“國有商業(yè)航母”無疑是零售業(yè)繞不過去的關鍵詞。當業(yè)內(nèi)繼續(xù)對“百聯(lián)模式”反思的時候,其效仿者———武漢商聯(lián)(集團)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“武商聯(lián)集團”)于5月16日正式揭牌。與此同時,北京西單友誼集團、王府井百貨集團、城鄉(xiāng)貿(mào)易等三家重組的消息也不絕于耳。
事實上,在如何打造國有商業(yè)航母這道考題前,各地政府的教訓遠遠多于經(jīng)驗。在我國市場經(jīng)濟日益成熟的今天,利用行政力量組建“商業(yè)航母”并非國有商業(yè)企業(yè)改革的全部,而只是國有商業(yè)做強做大的萬里長征的第一步。
“百聯(lián)”標本
目前我國國有商業(yè)企業(yè)改革或者說國有資本退出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情況:一是國資“全面退出”,像東北、西北地區(qū)等。二是通過股份制改革在結構上適當調(diào)整。三是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強勢整合,組建商業(yè)航母,如上海、重慶、北京、武漢等。
自從百聯(lián)集團的大手筆案例產(chǎn)生后,“百聯(lián)模式”似乎被業(yè)界尤其是各地政府所更多地推崇。尤其是今年武漢國資委在重組武漢商業(yè)過程中,在權衡了百聯(lián)模式和“民資嫁接”方式后,最后決定決不吸收戰(zhàn)略資本,更是將“百聯(lián)模式”演繹到了極致。
當然,這種模式的好處在于通過行政性的資產(chǎn)合并重組,將產(chǎn)業(yè)集中于商業(yè)流通領域,之后通過整體上市融資,可以做大做強、增強整體實力,最終實現(xiàn)與以沃爾瑪為代表的外資零售大鱷抗爭的戰(zhàn)略目的。
眼下,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本土商業(yè)是否會成為開放的犧牲品,擔憂沒有超級長線資本進駐的本土商業(yè)何以抵抗來自瘋狂擴張的國外超級大鱷的蠶食,感嘆我國國有資本的弱小。或許,當自由市場規(guī)則明顯有利于占盡優(yōu)勢的龐大的國外資本,當博弈雙方力量相差太懸殊,而這個行業(yè)又事關國家經(jīng)濟安全的時候,通過國有股轉讓方式進行國家資源整合,是離市場方式最近的一條改善實力平衡的捷徑。
不過,有專家直言,對抗沃爾瑪們的做大做強僅僅是重組的表面動因,更深一層的動因還在于:在向“市場經(jīng)濟國家”轉型的進程中,產(chǎn)權多元化、國有資產(chǎn)淡出沒有明顯競爭優(yōu)勢的商業(yè)零售領域是大勢所趨,而要實現(xiàn)戰(zhàn)略性的轉移,國有的商業(yè)零售企業(yè)必然要通過行政或市場的重組手段進行改制。
對于各地紛紛組建商業(yè)集團,上海某商界人士也強調(diào),就是對國資退出方式途徑的探索。他認為,如果上海幾大商貿(mào)集團的國資只是簡單地依據(jù)賬面價值退出,方法可能比較簡單易行,但是國資沒有實現(xiàn)它的最大價值,是要吃虧的。而通過整合,把百聯(lián)做強做大,也就是把國資的蛋糕做大,在此基礎上再以實現(xiàn)股權的多元化退出,就可以使得國資在退出的時候實現(xiàn)收益最大化。不然在組建百聯(lián)集團時,除了華聯(lián)、一百、友誼之外,經(jīng)營不善幾乎資不抵債的上海物資集團就不會被納入其中了。
百聯(lián)集團原董事長張新生曾在公開場合也表示,百聯(lián)集團將采取“包裝整合—壯大規(guī)模—股權轉讓—國際化”的改制模式,通過這種模式,國有資本如果退出可以賣個好價錢;如果不退出也可以繼續(xù)保值增值。而在某種意義上講,重資產(chǎn)、輕企業(yè)正是百聯(lián)模式的精髓。
因此,單純從產(chǎn)權上講,作為國企資產(chǎn)的所有者國資委,他們通過整合的方式來調(diào)劑資產(chǎn)于法于理無可厚非。尤其是在國有企業(yè),由于一系列的歷史遺留問題,單純靠企業(yè)自身來運作還遠遠不夠,所以在重組過程中政府的介入很有必要。
代價昂貴
盡管在組建“商業(yè)航母”問題上至今仍爭議不斷,但上海、武漢、重慶等地依舊按原有的思路行事,甚至依靠行政力量和行政思維去經(jīng)營整合后的優(yōu)良資產(chǎn)。當然,政府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。
目前,凡是重組后的新集團的高級管理層基本上還都是行政任命,管理體系沒有發(fā)生根本變化,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糾纏不清的利益關系,使“洋人”羨慕不已的優(yōu)質資產(chǎn)和龐大的中央采購能力無法得以發(fā)揮,專業(yè)化管理難以實現(xiàn),國有資本的控制權和股東利益最大化之間始終無法取得較好的平衡。
中國社科院財貿(mào)所趙萍博士曾經(jīng)不無感慨地說:“流通業(yè)中,很多合并的成果中,業(yè)務模式和采購渠道仍然分道揚鑣。”
一家外資零售商也表示:“在國外,要進行企業(yè)之間的合并重組是一種市場行為,企業(yè)對各自的資金支配、人員先做好統(tǒng)籌安排,再坐下來談合并的事宜。”在他們看來,這些由政府“撮合”而非市場形成的商業(yè)航母,雖然能夠形成規(guī)模優(yōu)勢,但規(guī)模并不等于核心競爭力,凱瑪特已經(jīng)發(fā)展到很大了,而最后的破產(chǎn)也就是瞬間的事情。
現(xiàn)在不妨看看百聯(lián)集團的現(xiàn)狀。2006年,百聯(lián)集團突發(fā)人事震蕩。先是集團董事長張新生在當年4月被調(diào)上海市經(jīng)委;5月,集團總裁王宗南兼任新光明食品集團籌備組成員,8月便正式調(diào)任光明食品集團董事長。百聯(lián)集團2007年經(jīng)濟工作研討會上透露的信息顯示,2006年該集團銷售規(guī)模為1400多億元,主營業(yè)務收入600多億元,但利潤只有9億元左右。最近,坊間又盛傳,張新生有再回百聯(lián)集團的可能。
除了人事任免的繁雜外,這些“商業(yè)航母”都將面臨業(yè)態(tài)整合如何體現(xiàn)利益最大化的問題。百聯(lián)集團中,著名的“華聯(lián)”品牌蕩然無存,被新華傳媒“借殼”,這讓許多熟悉華聯(lián)的人唏噓不已。武漢中商也面臨著這種命運———從目前來看,武昌中南路上的中南商業(yè)大樓、中南百貨和中南購物中心所形成的商圈,儼然與武廣、世貿(mào)以及新武商形成的商圈遙相呼應,一旦“中商”品牌消失,很多已經(jīng)存在的巨大品牌知名度和競爭優(yōu)勢也會喪失。
興業(yè)證券分析師認為,目前市場對于具有整合概念的企業(yè)普遍看好,但武商聯(lián)集團成立后短期難見具體整合步驟。武商聯(lián)集團自己也承認,由于歷史原因,鄂武商、武漢中百、武漢中商3家上市公司的同業(yè)競爭問題還將在一段時期內(nèi)存在。
至于西單友誼集團、王府井百貨集團以及城鄉(xiāng)貿(mào)易3家企業(yè)的重組,業(yè)內(nèi)人士也大都持謹慎態(tài)度。一個理由是,西單、王府井都是京城商業(yè)的金字招牌,重組肯定會造成商業(yè)品牌損失。
謹慎行政
然而,正如地域性很強的零售行業(yè)一樣,各地國有商業(yè)企業(yè)乃至政府部門都有著各自的特點和情況。
例如,掛牌后,武商聯(lián)集團將分別持有鄂武商A、武漢中百、武漢中商17.23%、10.10%和45.81%的股份,但問題是,武漢市政府對3家上市的控制力究竟有多大呢?公開數(shù)據(jù)顯示,武漢市國資公司在3家上市公司中所占的股份,最高時分別為41.94%、19.62%、59.32%。
顯然,武商聯(lián)集團控股后,3家公司股權依然分散,特別是“銀泰系”在二級市場依然有增持的可能,其在聯(lián)交所上市之時也明確表示將拿出大量資金用于收購,但一年內(nèi)應該不會與武商聯(lián)集團正面交火。目前,浙江銀泰百貨穩(wěn)坐鄂武商A的第二大股東位置。
其次,從外部環(huán)境看,武漢市此時重組商業(yè)是不是為時已晚呢?一位武漢商業(yè)企業(yè)的董事長表示,上世紀90年代末期政府初次提出重組商業(yè)時,他非常贊成。那時候武漢的外資并不很多,如果重組成功還能與外資一較高下。
隨著零售業(yè)全面開放,外資商業(yè)在武漢投資迅速增長。沃爾瑪、家樂福、麥德龍等一批世界知名的跨國商業(yè)集團齊駐武漢,并已實現(xiàn)由單店向多店發(fā)展。更令武漢本土商業(yè)企業(yè)感到不平的是,這些國際巨頭不僅占據(jù)著黃金位置,而且還享受到許多“超國民待遇”。據(jù)悉,麥德龍在武漢的用地是免費的。武漢市政府甚至還對外資做出了“返還3年利稅”的承諾。這種情況下,商業(yè)重組還能取得與外資抗衡的預期效果嗎?
具體到北京市國有商業(yè)重組,商務部一位官員分析認為,上海百聯(lián)集團之所以能順利成立,與上海市政府對企業(yè)負債、人員等具有強大的消化處理能力有關;而北京市政府不夠強勢或許正是西單友誼集團、王府井百貨集團以及城鄉(xiāng)貿(mào)易3家國有企業(yè)遲遲不能重組的原因。
拋開這些技術上的難題,一些業(yè)內(nèi)專家則從法律層面謹慎表示了對組建“商業(yè)航母”的看法。“《反壟斷法》之所以拖了13年才獲通過,難就難在對行政壟斷的態(tài)度上。我國零售業(yè)市場集中度不高,原因也在于行政壟斷。”一位業(yè)內(nèi)專家認為,“流通業(yè)的本質要求商品各要素要自由流動,目前一些地方的不公平政策以及地區(qū)封鎖阻礙了流通業(yè)的健康發(fā)展。”
他舉例說,目前國有獨資流通企業(yè)以及外資企業(yè)“吃小灶”的現(xiàn)象還大量存在,這些企業(yè)往往能夠享受特殊的政策。“不管這些企業(yè)的市場份額有多大,政府的做法都產(chǎn)生了歧視,從而導致這些企業(yè)的市場份額不是通過充分競爭得到的,政府也有行政壟斷的嫌疑。”他進一步質疑,眼下由政府出面撮合的“商業(yè)航母”是否也屬于行政壟斷呢?
該專家表示,《反壟斷法》將對企業(yè)以及政府的慣有思維模式形成沖擊,像政府以前“抓大放小”的提法估計也得“掂量”一下了。
有人則反駁說,2003年我國出現(xiàn)“非典”疫情后,一些城市的商品被搶購一空,當政府決定緊急借調(diào)某大型外資零售企業(yè)的商品時,該企業(yè)卻表示需要向國外總部匯報。“正是從那時起,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民族商業(yè)的政策,其中就包括加快培育大型流通企業(yè)。”
對此,該專家表示:“今后在政企分離的情況下,應建立政府花錢買服務的意識,可以規(guī)定外資流通企業(yè)在做大的時候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。”
不做“婆婆”
時至今日,政企分開、所有權和經(jīng)營權的分離已經(jīng)成為耳熟能詳?shù)脑~匯。業(yè)內(nèi)人士認為,對于“商業(yè)航母”,應該是讓優(yōu)質的國有資源按照市場的法則去組合,讓這些優(yōu)化組合后的資產(chǎn)給市場上最能干的人去經(jīng)營。各地政府既然有魄力和能力打破利益關系的阻撓創(chuàng)建國家和區(qū)域級商業(yè)龍頭,勇敢和堅毅地邁出了第一步,那么,就沒理由不能跨出優(yōu)化組合、任人惟賢、專業(yè)化管理的第二步。
毋庸質疑,以市場經(jīng)濟的規(guī)律來考量,建立現(xiàn)代企業(yè)制度、引入職業(yè)經(jīng)理人才是做大做強的前提。僅僅是通過在國有資產(chǎn)性質范圍內(nèi)的行政性重組,不通過市場的手段嫁接多種經(jīng)濟成分,重組后的企業(yè)依然是國有企業(yè),其資產(chǎn)“所有者缺位”的問題還是在所難免。
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國雄認為,沒有機制的轉換,重組僅僅是數(shù)量的擴張,這樣重組的企業(yè)不會走得太遠。他提出,國有企業(yè)并購重組,不要把同一種所有制、同一組織形式的企業(yè)強行捏在一起,必須引進外資和民營資本。因為同一所有制企業(yè)重組,機制沒有變化,這樣的重組,不是優(yōu)勢一加一大于二,而是問題一加一大于二。資產(chǎn)重組的目的是促成機制的轉換,實現(xiàn)優(yōu)勢互補。
“政府作為出資人,只需盡到自己相應的責任就行了,至于董事長等企業(yè)高層的變更一定要規(guī)范、透明,按現(xiàn)代企業(yè)制度要求去做。”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洪濤認為,我國流通業(yè)的職業(yè)經(jīng)理人機制雖然還不完善,但如果要更換企業(yè)高層領導,政府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選人,經(jīng)過董事會選舉決定。“政府不應該人、財、物都要管,要管那些企業(yè)自己做不了的事情。”
許多業(yè)內(nèi)專家建議,政府應設立出資人機構,與公共管理職能部門分開,受政府委托集中統(tǒng)一行使國家所有權。行使公共權利的部門不再承擔出資人職能,形成政企(資)分開的體制基礎,但決不能成為“婆婆加老板”,直接干預企業(yè)的生產(chǎn)經(jīng)營。
去年,商務部商業(yè)改革司邸建凱司長在商務部網(wǎng)站“在線訪談”接受提問時也表示:“流通企業(yè)在做大規(guī)模的同時,一定要加快產(chǎn)權制度改革步伐,建立健全現(xiàn)代企業(yè)制度。”
(作者:超市周刊特約撰稿人 洪森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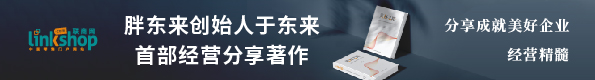







發(fā)表評論
登錄 | 注冊